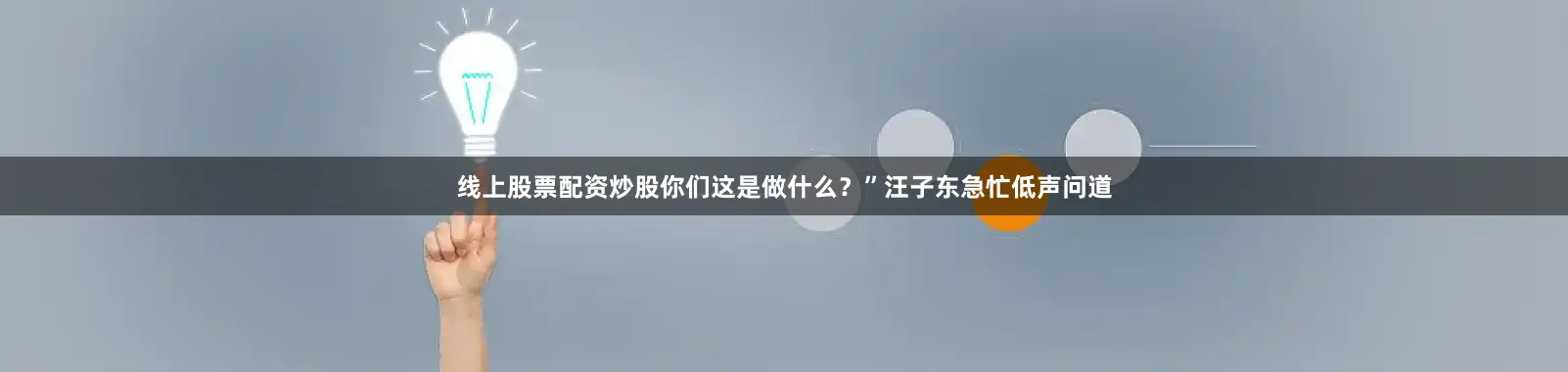
改写后的版本:
1944年12月的某一天,安徽芜湖,汪公馆门前热闹非凡,车水马龙。周围弥漫着哀乐的旋律,一场肃穆的葬礼即将举行——汪子东母亲的丧事。
汪子东,原籍浙江绍兴,早年曾前往日本留学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他投身汪伪政权,成为了一个臭名昭著的汉奸,并被任命为汪伪商业部副部长以及芜湖军需部长。他在汪伪政权中权势滔天,是汪精卫身边的宠臣。汪子东的地位使得那些小汉奸难以接近他,而汪母的葬礼成了一个极好的巴结机会。于是,汪公馆门前聚集了大批来吊唁和送礼的人。
中午时分,一个身穿长衫、身材魁梧的男子出现在汪公馆门前,他大约三十多岁,随行还有五六个身穿便服的随从。男子走进汪公馆,随从们便开始奉上厚重的礼物。男子按照礼节,先在灵堂前烧香,随后跪拜,声音带着哽咽,“伯母,小侄来迟了!”
汪子东看得目瞪口呆,心中升起了疑惑。这人面生得很,他上下打量着他,还是无法回忆起在何时见过。“这位兄弟,我怎么不记得你?”汪子东迷惑地问道。
展开剩余82%男子听后,愈加伤感,嗓音中透着颤抖:“堂弟,你现在风头更劲了,连我这个堂兄都认不出来了,我是汪子安啊。”他又接着说道,“几日前在上海听绍兴的老乡说伯母去世,得知后我急忙赶来吊丧。”说完,他拉住汪子东的手,示意他一起走向后院。
汪子东依然不解,边走边喃喃自语:“我怎么完全不记得有你这个堂兄?”话音未落,突然感到后脑勺一阵凉意,似乎有什么东西顶住了他的脑袋。
这种感觉让汪子东打了个寒战,差点失去平衡。他的直觉告诉他,那一定是冰冷的枪口,身体一颤,几乎摔倒在地。
“兄弟,有话好好说,你们这是做什么?”汪子东急忙低声问道。
“我们是新四军,别多嘴!”来者低声冷笑道。
汪子东迅速回忆起四周,低声回应:“公馆里外都是我的人……”
那人听后冷笑一声:“我知道你的人多,但你喊试试看,我一声令下,立刻送你见阎王!”
汪子东的胆量瞬间被吓破,顿时像泄气的皮球一样,声音也软了下来。他从未真正经历过血腥的战斗,胆怯的他此刻终于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。
“有什么事咱们好好谈,能不能先放下枪?子弹不会分辨人,如果走火怎么办?”汪子东说道。
听到这话,那人终于松开了枪,露出了自己的身份,接着也透露了来意。
“我是叶进明,来自浙江余姚。17岁时我便参加了革命,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。新四军成立后,我担任总兵站站长,也兼任第七师的供给部长,负责军需物资和财政。”
叶进明继续说道:“这份工作不轻松,尤其是在日伪和顽固派的封锁下,想要为新四军提供稳定的物资保障,几乎不可能。但我凭借一腔忠诚和精明的办事能力,做得有声有色,得到了上级的好评。”
1944年12月,战局突然发生了变化,日军节节败退,反攻的时机即将到来。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将一项艰巨的任务交给叶进明:筹集充足的粮款和物资,为即将到来的大反攻做准备。
叶进明带着警卫员直奔新四军第七师驻地——安徽无为县的团山镇。
在新四军的老兵中,曾流传过这样一句话:“一师打的仗多,二师出的干部多,三师拔掉的据点多,四师养马多,五师占领的地盘多,六师跑的路程多,七师上交的银子多。”
第七师兵力不算强大,虽然很少直接参战,但其驻地的自然条件优越,是鱼米之乡,兵员和资源丰富,为新四军提供了大量的后勤支持。
叶进明来到了第七师的驻地,在与师长谭希林和政委曾希圣会面后,发现了意外的惊喜:在一个大祠堂内,堆积如山的白花花的大米,仿佛一座粮山。
叶进明惊喜地问:“谭师长,您怎么搞到这么多粮食?”
谭希林笑道:“芜湖是全国知名的米市,粮食筹集起来轻而易举。”
“太好了,任务终于能顺利完成了!”叶进明高兴地说道。
然而,曾希圣提醒他:“这么多粮食若不变现,根本无法派上用场。问题是如何将这些粮食换成银子和军需物资。”
叶进明深思熟虑后问:“附近有码头吗?”
“有的,”谭希林答道,“不远处有一个叫汤沟的小镇,是一个大码头,虽然被日伪控制,但不妨碍我们使用。”
叶进明听后皱了皱眉,“那就有些麻烦了。”
曾希圣接着说:“不过如果我们换上便衣,日伪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假装看不见。但这些粮食不好变现,卖了也没有地方交换军需物资。”
正当此时,谭希林突然一拍脑袋:“我怎么没想到!我们可以找汪子东帮忙!”
汪子东,虽然是一个汉奸,但曾在日本留学,和汪精卫是同乡,两人的祖辈关系密切,汪子东因此在伪政权中得到了极高的职位。虽然他是汉奸,但并没有亲自沾染血腥,毕竟他只是一个文化人,未必完全心狠手辣。
巧的是,汪子东的母亲刚刚去世,他正忙于筹办丧事。叶进明听后,决定前去汪公馆接触他。
于是,叶进明冒充“侄子”,带着随从前去汪公馆吊丧。
发布于:天津市倍悦网-实盘配资开户-a股加杠杆-加杠杆怎么炒股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